发布日期:
乡村听夏
文章字数:1071
■福建厦门 林月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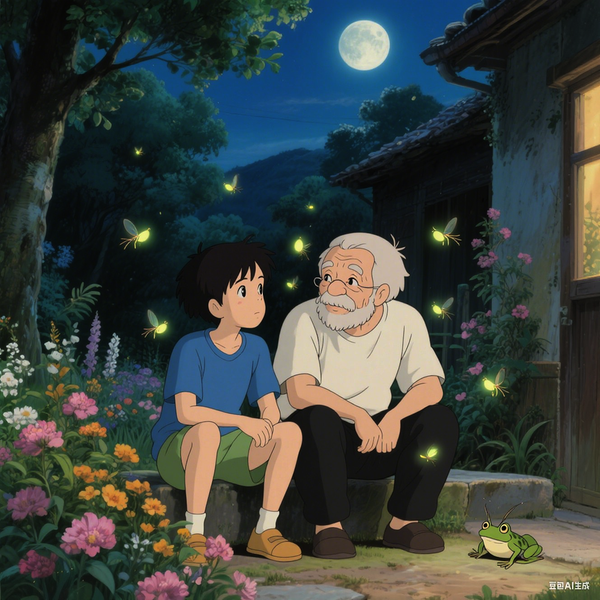
盛夏的闽南乡下,是声浪织就的画卷。这些声音,是乡野的呼吸,是记忆的刻刀,将我对故乡的眷恋,一刀刀凿进岁月的年轮。
蝉声,是夏日最灼热的宣言。黑蚱蝉栖在苦楝树枝桠上,腹部如滚烫的铁器,每一声嘶鸣都震得叶片簌簌发抖。它们以阔叶林为舞台,以梧桐树为麦克风,将求偶的呐喊化作滚烫的热浪。我曾见过蝉蜕悬在竹篱上,空壳如半透明的琥珀,仿佛凝固了生命最后的嘶吼。
蛙声,是荷塘最灵动的诗行。沼水蛙的短促鸣叫如急雨敲打青石板,饰纹姬蛙的长吟似丝竹缠绕稻穗。夜幕初垂时,蛙声从池塘深处浮起,层层叠叠漫过田埂,惊醒了沉睡的萤火虫。我常蹲在塘边石阶上,看蛙群在月光下跃动,听它们的合唱穿透荷叶的脉络,将水波推成一圈圈银亮的涟漪。
鸟鸣,是晨光最清脆的铃铛。百灵鸟衔着第一缕风掠过竹林,啼声如琉璃碎裂,撒成一串跳跃的音符。麻雀在屋檐下啄食米粒,叽喳声像孩童的嬉闹,溅起晨雾的微光。最难忘的是布谷鸟的呼唤——“布谷!布谷!”那声音悠长而辽远,仿佛穿透了山峦的褶皱,催促农人下田劳作。
溪流,是山间最缠绵的絮语。涧水从石缝间渗出,叮咚声如古琴拨弦,清泠泠地淌过青苔覆盖的卵石。雨后,溪流暴涨成银色的瀑布,裹挟着落叶与碎花,冲刷着岸边的芦苇丛。我常赤脚踩进水中,让凉意从脚趾渗入血脉,听水流在石缝间迂回,将蝉鸣、蛙声、鸟啼都揉碎成细密的泡沫。
雷雨,是天公最暴烈的狂欢。闷热的午后,乌云压得竹楼喘不过气,忽有惊雷劈开天幕,炸裂声如万马奔腾,震得瓦片簌簌震颤。雨点砸在屋顶,迸出清脆的爆裂声;溪流霎时涨成银色的洪流,将青苔冲刷成苍白的伤痕。我蜷在阿嬷的竹床上,听雨声与蛙鸣交织成一片,恍惚间,仿佛听见大地在暴雨中哼唱古老的童谣。雨停后,蝉声从湿漉漉的树冠里复苏,蛙声从积水的洼地重新浮起,溪流又恢复了叮咚的韵律,仿佛一切喧嚣,不过是夏日一场酣畅的醉梦。
风声,是乡村最温柔的耳语。晨起时,东南风裹着海盐的气息掠过晒谷场,稻草堆沙沙作响,像无数双无形的手在翻阅金黄的诗卷;夜深人静时,西北风从古厝的砖缝钻入,卷起竹席上的残梦,将芭蕉叶的低语传向远方。有时风会停驻在晒衣绳上,蓝布衫随风摆动,发出布料摩擦的簌簌声,恍若阿嬷在絮叨未说完的故事。
这些声音,是乡愁的密码。蝉鸣里藏着祖辈在树荫下纳凉的汗渍,蛙声中回荡着阿嬷摇蒲扇的吟唱,溪流声浸润了少年赤脚捉鱼的欢笑。如今,城市霓虹淹没自然的韵律,而我仍固执地守着这份弥足珍贵的乡音——它不仅是听觉的盛宴,更是闽南人血脉里的基因。
当蝉蜕再次爬上老树,当蛙声在荷塘复响,我忽然明白:那些被钢筋水泥困住的灵魂,终将在自然的交响中寻回失落的故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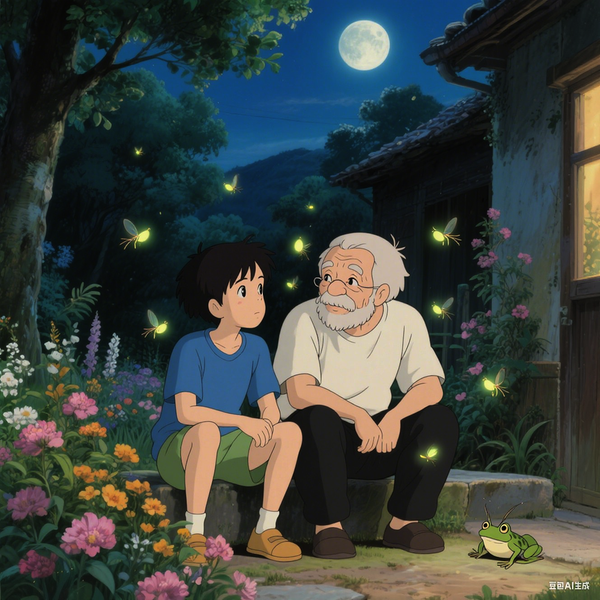
盛夏的闽南乡下,是声浪织就的画卷。这些声音,是乡野的呼吸,是记忆的刻刀,将我对故乡的眷恋,一刀刀凿进岁月的年轮。
蝉声,是夏日最灼热的宣言。黑蚱蝉栖在苦楝树枝桠上,腹部如滚烫的铁器,每一声嘶鸣都震得叶片簌簌发抖。它们以阔叶林为舞台,以梧桐树为麦克风,将求偶的呐喊化作滚烫的热浪。我曾见过蝉蜕悬在竹篱上,空壳如半透明的琥珀,仿佛凝固了生命最后的嘶吼。
蛙声,是荷塘最灵动的诗行。沼水蛙的短促鸣叫如急雨敲打青石板,饰纹姬蛙的长吟似丝竹缠绕稻穗。夜幕初垂时,蛙声从池塘深处浮起,层层叠叠漫过田埂,惊醒了沉睡的萤火虫。我常蹲在塘边石阶上,看蛙群在月光下跃动,听它们的合唱穿透荷叶的脉络,将水波推成一圈圈银亮的涟漪。
鸟鸣,是晨光最清脆的铃铛。百灵鸟衔着第一缕风掠过竹林,啼声如琉璃碎裂,撒成一串跳跃的音符。麻雀在屋檐下啄食米粒,叽喳声像孩童的嬉闹,溅起晨雾的微光。最难忘的是布谷鸟的呼唤——“布谷!布谷!”那声音悠长而辽远,仿佛穿透了山峦的褶皱,催促农人下田劳作。
溪流,是山间最缠绵的絮语。涧水从石缝间渗出,叮咚声如古琴拨弦,清泠泠地淌过青苔覆盖的卵石。雨后,溪流暴涨成银色的瀑布,裹挟着落叶与碎花,冲刷着岸边的芦苇丛。我常赤脚踩进水中,让凉意从脚趾渗入血脉,听水流在石缝间迂回,将蝉鸣、蛙声、鸟啼都揉碎成细密的泡沫。
雷雨,是天公最暴烈的狂欢。闷热的午后,乌云压得竹楼喘不过气,忽有惊雷劈开天幕,炸裂声如万马奔腾,震得瓦片簌簌震颤。雨点砸在屋顶,迸出清脆的爆裂声;溪流霎时涨成银色的洪流,将青苔冲刷成苍白的伤痕。我蜷在阿嬷的竹床上,听雨声与蛙鸣交织成一片,恍惚间,仿佛听见大地在暴雨中哼唱古老的童谣。雨停后,蝉声从湿漉漉的树冠里复苏,蛙声从积水的洼地重新浮起,溪流又恢复了叮咚的韵律,仿佛一切喧嚣,不过是夏日一场酣畅的醉梦。
风声,是乡村最温柔的耳语。晨起时,东南风裹着海盐的气息掠过晒谷场,稻草堆沙沙作响,像无数双无形的手在翻阅金黄的诗卷;夜深人静时,西北风从古厝的砖缝钻入,卷起竹席上的残梦,将芭蕉叶的低语传向远方。有时风会停驻在晒衣绳上,蓝布衫随风摆动,发出布料摩擦的簌簌声,恍若阿嬷在絮叨未说完的故事。
这些声音,是乡愁的密码。蝉鸣里藏着祖辈在树荫下纳凉的汗渍,蛙声中回荡着阿嬷摇蒲扇的吟唱,溪流声浸润了少年赤脚捉鱼的欢笑。如今,城市霓虹淹没自然的韵律,而我仍固执地守着这份弥足珍贵的乡音——它不仅是听觉的盛宴,更是闽南人血脉里的基因。
当蝉蜕再次爬上老树,当蛙声在荷塘复响,我忽然明白:那些被钢筋水泥困住的灵魂,终将在自然的交响中寻回失落的故乡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