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日期:
心灵的回归
文章字数:56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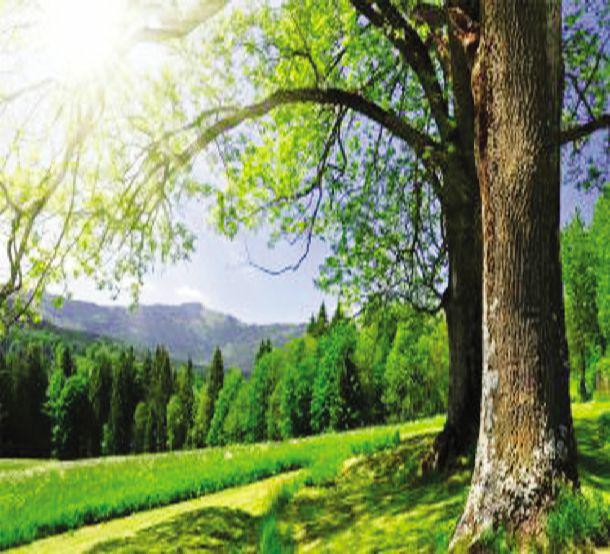
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一条消息,重庆打通镇吹角村打造了一个千亩紫薇花观赏基地,每逢周末,许多城里的上班族都开车到吹角村紫薇花农家乐度周末,吃农家菜,赏花,吸氧,带着孩子在鱼塘里钓鱼,在小河里抓螃蟹。吹角,也是我儿时生活的地方,我的故乡。
四十年前,父母在那里当乡村教师,我在那里无忧无虑地成长,几年后父亲便担任吹角乡初级中学校长。我初中毕业离开了吹角,从此走进城里求学,工作。后来,撤乡并镇,吹角乡改为吹角村,吹角乡初级中学与打通镇中学合并,更名为綦江区打通中学,父亲成了打通中学的教师,继续坚守在三尺讲台。
回到老家,儿子举着单反相机为我和我那些儿时的小伙伴照相,突然发现我和小伙伴的脸上的皮肤都有点苍老了,不过,沧桑的脸更显得成熟,比年轻时稚嫩的脸蛋更有味道。不同的脸记录着不同的年龄和经历,根本无需为容颜的变老而叹息,更不必为财富的多少而焦虑。阿兰德波顿在《身份的焦虑》中提出,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有两种途径:要么努力取得更高的成就,要么降低对自我的期望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对阿兰德波顿的话理解得越来越透彻,我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。我那些儿时的伙伴之所以过得很幸福,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期待值并不高。我也越来越理解父亲年轻时,为什么安心于当一名乡村教师?因为他对自己的期待值不高。父亲的选择并没有错,因为他过得很幸福。(金泽明)
